「你們都同居了,我們親戚鄰居都知道,在老家這就是夫妻了啊!現在說分手,你以後還怎麼嫁人?你不覺得丟人嗎?」
齊父也點頭:「而且你帶著個孩子,除了明遠,誰還敢要你?我們是為你好,別不知好歹了!」
齊小凡抓著我的裙角:「媽媽……媽媽我真的錯了。我不想待在孤兒院,我還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……」
我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我居高臨下地看著那三張可憐兮兮的臉,慢條斯理道:
「你們現在去問問,看看是我秦薇薇沒人要,還是你們家兒子前途盡毀?」
「齊小凡,你現在想起來喊我媽了?」
「可惜啊,我本來給你準備了去美國的夏令營,不過你既然說我總是逼你學習,你放心,以後你想學,也沒機會了。」
「這孩子我可不帶。你們願意要,就帶走。不願意要就找個地方扔了。」
我說完,頭也不回地轉身走進別墅。
我再次見到齊明遠,是在庭審那天。
他因惡意轉移財產、欠債拒不歸還,構成經濟詐騙,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,緩刑一年。
這一次,他竟然難得地沒有撒潑。
庭審結束後,我們再次面對面坐了下來。
他眼圈通紅,嗓子發啞:
「薇薇……我知道我對不起你。我那時候是鬼迷心竅,我以為你不會離開我……」
「我從來沒想過和蔣潔在一起,她只是個小插曲,你才是主旋律。我,我是被偏愛的人有恃無恐……」
我忍不住笑了:「你音樂學得不錯啊?」
他急得抬起頭:「真的!她根本就不如你,無論是樣貌、能力、一切的一切……」
我站起來:「謝謝你的肯定。我還沒淪落到要和她比高低。」
他顫抖一下,他應該早就意識到,曾經屬於他的那個我,真的已經永遠離開了。
蔣潔逃出京城以後,灰頭土臉地回了老家。
可她再也不是那個能靠幾張自拍照就在網上收割濾鏡、博得憐憫的小白花了。
她的名字早就被網友扒得一清二楚,私德敗壞、職場霸凌、偷情當小三……哪一條拎出來都夠讓她在縣城名聲掃地。
她剛落地,就聽見鄰里街坊在背後指指點點。
她開始宣揚是齊明遠騙了她,甚至在縣城最大的商場門口大喊大叫,被幾個看不下去的大媽圍起來罵了半個小時。
她成了鎮上遠近聞名的祥林嫂,她和齊明遠這對狗男女的惡事也成了街頭巷尾的笑話。
有一天,她正在罵街,被回老家賣房抵債的齊明遠撞了個正著。
他上來就是一巴掌,把蔣潔扇得摔進泥地。
接著又是一頓拳打腳踢,甚至抄起了鐵杴。
蔣潔被送進了醫院,左腿粉碎性骨折,徹底落下了殘疾。
後來,她在老家租的小屋裡,打開燃氣灶自殺了。
網上傳來消息時,我正在和一個新朋友共進晚餐。
他叫裴斯年,是我在一次慈善拍賣會上認識的投資人。
我們坐在最頂級的一家法餐廳,他忽然從懷裡掏出一個絲絨盒,說是送我的禮物。
我疑惑地打開,裡面竟是我當時丟的藍鑽耳釘。
「你在哪裡找到的?」我驚喜地問。
他笑了笑:「剛好掉到了我家游泳池裡,你說是不是緣分?」
我盯著他的眼睛看,他眸子裡藏著玩味。顯然是在撒謊。
「你撒謊。」我低聲說。
他舉杯朝我晃了晃:「那天恰好我也在。你走後,我知道這東西對你來說非常珍貴,所以掘地三尺,為你拿了回來。」
我一時語塞,只覺得那枚藍鑽灼得手心發燙。
「願意嫁給我嗎?」他溫柔地問。
我怔了怔,心跳卻莫名漏了一拍。
他側頭看我:「你不必現在回答我,我可以等。」
我們十指相扣,走出餐廳大門。
夜風撲面而來,在這番美好的景色中,我看到了一個不合宜的身影。
一個臉上髒污不堪的孩子,身上穿著一件已經洗得發灰、還破了個洞的孤兒院舊棉衣。
齊小凡。
那個曾抓著我的裙子要糖吃,後來對著我臉吐口水,惡毒叫我「賤人」的孩子,如今成了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樣。
齊明遠進了監獄,我聽說齊家二老也嫌這孩子晦氣,要挾我無果後,就忙不迭地把他送回了孤兒院。
他不知道,那家孤兒院是我特意選的。
表面上是孤兒院,實際是一家管教中心。
所以齊小凡寧願流浪,也要逃出來。
他沖我跪爬著靠近兩步:「媽媽……你見過我的媽媽嗎?」
原來如此,他不認得我了。
畢竟在離開齊明遠和他之後,我減了二十斤體重,又變回了那個又美又颯的秦薇薇。
裴斯年看我一眼:「這孩子是誰?」
我搖頭:「不知道,不認識。」
這時,齊小凡似乎認出了我的聲音,他驚喜地抬起頭,下一秒,又嗚咽著哭起來:
「媽媽,我真的錯了……我好餓,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……你帶我回家吧……媽媽……」
我理都不理。
我從不是聖母。
我上了裴斯年的邁巴赫,門關上的瞬間,我看了眼倒影中那可憐蜷縮的小身影,唇角一勾。
正好,今晚心情不錯。
我打算加個甜點。
(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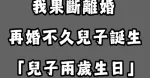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