繼父替生父養大我,如今我一年賺68萬繼父來借錢,我:200你收好
我看著桌上那兩張被繼父李建國用指尖摁得微微發皺的百元鈔票,心裡出奇地平靜。
我知道,從今天起,我陳默二十多年來在街坊鄰里口中那個「懂事、孝順、有出息」的好兒子名聲,算是徹底砸了。
也好。
這二十二年,像一場漫長而溫情的默片。從我八歲他走進這個家開始,他那雙布滿老繭的手,就成了我和我媽搖搖欲墜的天。他給我買第一輛鳳凰牌自行車,笨拙地跟在後面跑,摔得比我還狼狽;他手把手教我用烙鐵修好了鄰居家的收音機,讓我成了院裡孩子王;高三那年我半夜發高燒,是他用那輛破舊的三輪車,在凌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蹬得鏈條嘩嘩作響,把我送進了醫院。
所有人都說,李建國待我,比親生的還好。
我也一直這麼以為,深信不疑。
直到半小時前,他侷促地坐在我這套寬敞明亮的江景房裡,那雙常年勞作的粗糙大手,在我們家那張纖塵不染的胡桃木茶几上,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。他搓了很久,終於小心翼翼地開了口。
第1章 兩百塊錢
「阿默啊……」李建國清了清嗓子,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和緊張,「那個……你弟,李浩,不是要結婚了嘛。」
我點點頭,給他續上茶水,沒說話。
李浩是李建國和他前妻的兒子,比我小兩歲。當年李建國離婚時,李浩判給了前妻,但父子倆的聯繫一直沒斷。這些年,李浩上學、工作,李建國沒少往裡貼補。
「女方家裡……要求得有套婚房。」他端起茶杯,滾燙的茶水似乎給了他一點勇氣,「首付還差一些,我想著……你現在出息了,公司開得這麼大,能不能……先借叔三十萬?」
他說的是「借」,語氣卻卑微得像在「討」。
我看著他。五十出頭的年紀,頭髮已經花白了大半,眼角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一樣。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外套,袖口磨損得起了毛邊,和我這身定製的襯衫、腕上的手錶,以及這間屋子裡任何一件家具都顯得格格不入。
這就是那個把我從一個瘦弱、自卑的單親家庭孩子,一步步拉扯大的男人。那個會在冬天把我的手揣進他懷裡焐熱,會在夏天用蒲扇為我趕蚊子的男人。那個在我考上大學時,激動得在院子裡擺了三桌酒,逢人就說「我兒子有出息了」的男人。
三十萬。
對我如今一年六十八萬的凈收入來說,不算一個小數目,但也不是拿不出來。
我的沉默,似乎讓他更加不安。他放在膝蓋上的手,不自覺地攥緊了褲腿,關節因為用力而泛白。
「阿默,叔知道這錢不少,」他急急地補充道,「你放心,這錢算我借的!我給你打欠條!我跟現在身體還好,還能再干幾年,我們慢慢還,肯定能還上!」
我依然沒有說話,只是站起身,走進了書房。
李建國大概以為我同意了,渾濁的眼睛裡瞬間迸發出一絲光亮,整個人都鬆弛了下來,背脊也不再繃得那麼緊。
我能聽到客廳里他如釋重負的呼吸聲。
很快,我從書房裡出來,手裡拿著錢包。
李建國帶著期盼的目光迎向我。我走到他面前,從錢包里抽出兩張嶄新的百元鈔票,輕輕地放在了那張價值不菲的胡桃木茶几上。
「叔,」我開口,聲音平穩得連自己都覺得陌生,「這二百塊錢,你先拿著,給李浩買點水果,算是我這個當哥的一點心意。」
空氣,仿佛在這一瞬間凝固了。
李建國臉上的光,一點一點地熄滅下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然的、巨大的錯愕。他的嘴唇微微張著,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,似乎想說什麼,卻一個字也發不出來。
他死死地盯著桌上那兩張紅色的鈔票,那顏色刺眼得像一灘血。
「……阿默,你這是什麼意思?」過了足足有半分鐘,他才找回自己的聲音,乾澀、嘶啞,充滿了難以置信。
「沒什麼意思。」我拉開他對面的椅子,坐下,平靜地看著他,「李浩結婚是喜事,我這個當哥的,理應有所表示。但這錢,我不能借。」
「為什麼?」他的聲音陡然拔高,因為激動,臉頰漲得通紅,「三十萬對你來說,很難嗎?我不是不還!我是你爸啊,阿默!」
「你不是。」我輕輕地說出這三個字。
這三個字像一把冰冷的錐子,狠狠地扎進了他心裡。
李建國的身體劇烈地晃了一下,他撐著茶几的邊緣才勉強穩住。他看著我,眼神里混雜著震驚、受傷、憤怒,還有一絲我看不懂的慌亂。
「你……你說什麼?」
「我說,你不是我親爸。」我重複了一遍,語氣依舊平淡,但每個字都像淬了冰,「你姓李,我姓陳。這些年,你養我,辛苦了。這份恩情我記著,以後你和我媽的生活,我負責到底。但李浩的事,是你們李家的事,跟我這個外人,沒關係。」
「外人?」李建國像是聽到了天底下最荒謬的笑話,他指著我,手指因為憤怒而劇烈地顫抖,「陳默!你摸著你的良心說!我什麼時候拿你當過外人?你小時候生病,是誰背著你跑幾里地去衛生所?你上學的學費、生活費,哪一分不是我從牙縫裡省出來的?你現在出息了,有錢了,就跟我說你是外人了?」
他的質問聲聲泣血,每一個字都像一塊石頭砸在我的心上。
我當然記得。
我怎麼會忘。
八歲那年,我親生父親張志強,拋棄了我和我媽。家裡所有的積蓄都被他捲走了,我媽王秀蓮一個弱女子,帶著我,靠給人縫縫補補,日子過得朝不保夕。是李建國,一個工地上扛水泥的普通工人,走進了我們的生活。
他老實,本分,話不多,但對我和我媽是實打實的好。他會把工地上發的雞腿用飯盒裝好,帶回來給我吃,自己啃著干硬的饅頭。他會用廢舊的木料,給我做一把小木槍,一輛小推車。我們家那張用了十幾年的飯桌,有一條桌腿壞了,也是他找來木頭,叮叮噹噹地敲打了一個下午,修好的。
那條修補過的桌腿,就像他這個人一樣,沉默而堅實地,支撐著我們這個家。
這些恩情,我都記得。
可有些事,也只有我記得。
「叔,你別激動。」我深吸一口氣,試圖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更溫和一些,「我說了,你和我媽的養老,我全包。你想住什麼樣的房子,想去哪裡旅遊,想吃什麼用什麼,一句話的事。但李浩的婚房,這三十萬,我不會出。」
我的堅持,徹底點燃了李建國的怒火。
「好!好!好!」他連說三個「好」字,氣得胸膛劇烈起伏,「陳默,我真是養了條白眼狼!我李建國這輩子,算是看錯了人!」
他猛地一拍桌子,那兩張百元鈔票被震得跳了一下。
「這錢,我不要!」他吼道,「我李建國還沒到要飯的地步!」

說完,他頭也不回地沖向門口,用力拉開房門,又「砰」的一聲狠狠甩上。那巨大的關門聲,震得牆上的掛畫都晃了晃,也震得我的心,跟著一顫。
世界,終於安靜了。
我坐在空曠的客廳里,久久沒有動。陽光透過巨大的落地窗灑進來,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,溫暖而刺眼。
我低頭,看著茶几上那孤零零的兩百塊錢,嘴角泛起一絲苦澀的笑。
李建國,你以為我忘恩負義,以為我吝嗇刻薄。
你又怎麼會知道,我等這一天,等了整整十年。
第2章 那本存摺
李建國前腳剛走,我媽王秀蓮的電話後腳就追了過來。
電話一接通,她焦急的聲音就從聽筒里傳來:「阿默!你李叔是不是去找你了?你……你可千萬別惹他生氣啊!他那個人,好面子,你好好跟他說。」
我能想像到電話那頭,我媽急得團團轉的樣子。
「媽,他已經走了。」
「走了?」我媽的音調瞬間拔高,「怎麼就走了?事情……事情談得怎麼樣?他跟你借錢的事……」
「我沒借。」
電話那頭陷入了長久的沉默,只有微弱的電流聲在嘶嘶作響。過了好一會兒,我媽才用一種近乎嘆息的語氣說:「阿默,你怎麼能這樣……你李叔他對你怎麼樣,你心裡沒數嗎?三十萬,媽知道不是小數目,可你現在有這個能力,你弟弟就差這一步了,你怎麼能見死不救呢?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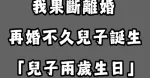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