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刻,我感覺到,我們之間的那道裂痕,正在慢慢癒合。
正月初七,預產期當天,我被推進了產房。
陣痛來臨的時候,我疼得幾乎暈厥過去。周建斌在外面急得團團轉,隔著門,我都能聽到他焦急的、帶著哭腔的聲音。
「晚秋!加油!你一定要挺住!」
「老婆!我愛你!你和孩子一定要平平安安的!」
經過十幾個小時的奮戰,我終於順利地產下了一個七斤二兩的胖小子,母子平安。
當護士把孩子抱出去的那一刻,我聽到了周建斌喜極而泣的哭聲。
回到病房,我筋疲力盡地躺在床上。周建斌握著我的手,眼睛腫得像核桃。他看著我,嘴唇動了動,千言萬語,最後只匯成了一句:「辛苦你了。」
我看著他,又看了看躺在我身邊,皺巴巴、紅彤彤的小傢伙,覺得之前所受的一切苦,都值了。
兩天後,公公婆婆風塵僕僕地從老家趕了過來。
他們是坐火車,再轉了好幾趟長途汽車,才輾轉來到市裡。那條出事的盤山公路,據說已經封了,要徹底整修,短時間內是通不了車了。

婆婆王秀蓮一進病房,看到我,眼圈就紅了。她沒敢靠近,只是遠遠地站著,搓著手,一臉的侷促和不安。
還是公公周大山,這個一輩子沉默寡言的男人,先開了口。他走到我床邊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「晚秋,爸對不住你。」
我愣住了,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反應。
婆婆也走了過來,拉著我的手,眼淚「唰」地就下來了。
「好孩子,是我們老糊塗了,是我們差點害了你……」她泣不成聲,「建斌都跟我們說了,要不是你堅持不回去,我們……我們這輩子都沒臉活了。」
她從一個布包里,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用紅布包著的東西,遞給我。
「這是……這是建斌他奶奶傳下來的一個銀鐲子,說是能保平安的。你拿著,就當是……我們給你賠罪了。」
我看著眼前這兩個滿臉風霜、寫滿愧疚的老人,心裡最後的一絲芥蒂,也煙消雲散了。他們不是惡人,他們只是被困在自己的認知和傳統里,不懂得如何用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愛。
那場災難,不僅敲醒了周建斌,也敲醒了他們。
我把鐲子推了回去,對我媽說:「媽,扶我起來一下。」
我靠在床頭,對著公公婆婆,露出了一個真誠的微笑。
「爸,媽,都過去了。你們來看我和寶寶,我很高興。」
第6章 看不見的守護
孩子滿月後,公公婆婆就回老家了。
臨走前,婆婆拉著我的手,絮絮叨叨地說了很多。她說,村裡那輛出事的小客車上,就有她一個遠房的侄子,二十多歲的小伙子,還沒結婚,就這麼沒了。她說,現在村裡的人一提起那件事,都後怕得不行。
「晚秋啊,」婆婆看著我的眼神里,帶著一種近乎敬畏的神色,「你是不是……有啥預感啊?要不咋就那麼巧,你死活不肯走呢?」
我笑了笑,沒有回答。
我該怎麼說呢?說我看到了一行血紅色的彈幕嗎?他們不會信,只會覺得是神鬼之說。
或許,就讓他們保留著這份敬畏,也挺好。至少,這能讓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裡,對生命多一份尊重,少一些固執。
送走了公公婆婆,我們的生活徹底回歸了平靜。
周建斌像一個模範丈夫和新手奶爸,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沖回來抱兒子。換尿布、喂奶、哄睡,他學得有模有樣,甚至比我這個當媽的還有耐心。
我們的交流也比以前多了很多。我們會一起討論孩子的未來,一起規劃家庭的開支,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,聊起各自工作上的煩惱。
他再也沒有對我提過任何強制性的要求,學會了用商量的語氣問我:「晚秋,你看這樣行不行?」
我知道,那場懸崖邊的危機,徹底改變了他,也重塑了我們的婚姻。我們不再是簡單地生活在一起,而是真正地成為了命運共同體。
有時候,夜裡看著身邊熟睡的父子倆,我還是會偶爾想起那行詭異的彈幕。
它到底是什麼?
是神靈的警示?是平行時空的預告?還是……別的什麼?
有一次,我媽來看外孫,我們聊起了我小時候的事情。
「你這孩子,從小第六感就特別准。」我媽抱著小寶,笑著說,「我記得你五歲那年,有一次你爸單位組織去鄰市的溶洞玩,全家都準備好了,你臨出門前突然抱著我的腿大哭,死活不肯上車,說車上有個紅眼睛的妖怪,會吃人。」
我有些茫然,對這件事毫無印象。
「我們當時都以為你是不想去幼兒園,故意找藉口,」我媽繼續說,「你爸氣得都要打你了。可你就是不鬆手,哭得撕心裂肺。最後沒辦法,我們一家就沒去成。」
「結果呢?」我好奇地問。
我媽的臉色嚴肅了起來:「結果,你爸他們單位那輛大巴車,在路上跟一輛貨車追尾了。雖然沒出人命,但車頭都撞爛了,坐在最前面的你爸的同事,腿斷了,眼睛也被碎玻璃劃傷了,縫了十幾針,一隻眼睛差點就瞎了。」
我聽得目瞪口呆。
「從那以後,你爸就總說,你是我們家的福星。」我媽感慨道,「他說你這孩子,能看見我們看不見的東西。」
聽完我媽的話,我陷入了長久的沉默。
或許,那行血紅色的彈幕,並不是什麼超自然的力量,而是我潛意識裡,一種被逼到極致的、來自母親本能的預警。
因為我太愛這個孩子,太想保護他,所以我的恐懼和擔憂,凝聚成了那樣一個具體而強烈的信號,一個不容我忽視、不容我妥協的最後通牒。
它是我作為母親,最原始、最強大的守護。
想通了這一點,我心中最後的一絲疑雲也消散了。
我不再去糾結那行字到底是什麼,我只知道,是它,也是我自己,共同守護了我的家庭。
春去秋來,小寶一天天長大,從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,長成了一個會笑會跑的淘氣包。他學會叫的第一個詞,不是「爸爸」,也不是「媽媽」,而是含糊不清的「家」。
周建斌的公司發展得很好,升了職,加了薪。我們換了一個大一點的房子,有了一個可以灑滿陽光的陽台。
他再也沒有提過要回老家過年。每年春節,都是我們一家三口,或者接我爸媽過來,一起過一個簡單而溫馨的年。他會定期給老家寄錢,打電話,用一種更理智、更成熟的方式,去盡他的孝道。
有一年夏天,我們一家三口去海邊度假。
傍晚,我和周建斌牽著手,走在柔軟的沙灘上,看著小寶在前面追逐著浪花,笑得咯咯作響。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。
「晚秋,」周建斌忽然停下腳步,認真地看著我,「這幾年,我常常會做同一個夢。」
「什麼夢?」
「我夢見,我開著車,載著你和孩子,行駛在那條山路上。然後,天就塌了……」他的聲音有些發緊,「每次,我都會從夢裡嚇醒,然後第一件事,就是摸摸你和孩子是不是還在我身邊。」
他握緊我的手,眼眶泛紅:「我才知道,什麼面子,什麼傳統,都是狗屁。你們平平安安地在我身邊,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我靠在他的肩膀上,看著遠處海天一色的壯麗景象,輕聲說:「我知道。」
是啊,我知道。
因為我也是。
那場未曾發生的災難,像一道深刻的烙印,刻在了我們夫妻的生命里。它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,幸福是多麼的脆弱,而家人的平安,又是多麼的可貴。
生活終究會歸於平淡,那些驚心動魄的過往,會慢慢沉澱成記憶的琥珀。
但有些東西,卻永遠地改變了。
比如,一個男人的成長,一段婚姻的堅韌,和一個母親心中,那份看不見的、卻足以抵擋一切風雨的守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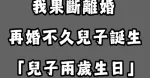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