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完,我掛斷了電話。
我知道我的做法很「冷血」,很「無情」。但我更清楚,有些傷口,需要時間來癒合;有些關係,需要距離來修復。一味的妥協和心軟,只會讓一切重回原點。
又過了半年,父親在電話里告訴我,姑父李建軍,那個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,一個人來我們家,帶了兩瓶酒,跟父親喝了一整夜。
據說,他哭得很傷心。
他說,自從工作調動的事情黃了之後,王秀蘭就像變了一個人,整天唉聲嘆氣,怨天尤人。家裡雞飛狗跳,不得安寧。兒子李浩也因為沒了指望,整天遊手好閒,不務正業。
他這才明白,這些年,他們一家人,一直都活在對我的依賴和索取中,早已喪失了獨立生活的能力。我這根「拐杖」突然被抽走,他們整個家都站不穩了。
「建國啊,」李建軍喝得滿臉通紅,拉著我父親的手說,「是我對不起你,對不起陳默。我們……我們把孩子的好,當成了驢肝肺。現在,我後悔啊!」
父親只是拍著他的肩膀,陪他一杯又一杯地喝著。
從那以後,王秀蘭一家,再也沒有主動聯繫過我。
第二年春節,我依舊回家過年。
除夕夜,我和父親兩個人,做了一桌簡單的年夜飯。沒有了往年的喧囂和爭吵,屋子裡顯得有些冷清,但也多了一份難得的溫馨和寧靜。
正吃著飯,院門被人輕輕敲響了。
父親去開門,門口站著的,是姑父李建軍,還有跟在他身後的王秀蘭和李浩。
他們三個人,手裡都提著東西,侷促地站在門口,不敢進來。
王秀蘭瘦了,也憔悴了,頭髮里夾雜著明顯的銀絲。她看著我,眼神躲閃,嘴唇蠕動了半天,才擠出一句話:「陳默……姑姑……姑姑來看看你。」
那一刻,我心裡的堅冰,似乎有了一絲融化的跡象。
我沒有說話,只是默默地轉身回屋,拿了三雙碗筷,放在了桌上。
父親明白了我的意思,連忙招呼他們:「快,快進來,外面冷。吃了沒?沒吃就一起吃點。」
那頓年夜飯,吃得異常沉默。
王秀蘭幾次想開口,但看到我平靜的臉,又把話咽了回去。
飯後,他們要走。臨出門前,王秀蘭突然轉過身,對著我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「陳默,對不起。」
她的聲音很輕,還帶著一絲沙啞,但每一個字,都清晰地傳到了我的耳朵里。
我沒有說「沒關係」。
因為有些傷害,一旦造成,就永遠無法真正抹平。
我只是對她點了點頭,說:「姑姑,新年快樂。」
看著他們一家三口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,我知道,我們之間的關係,可能再也回不到從前那種「親密無間」的狀態了。
但或許,這才是最好的結局。
我們終於學會了保持距離,學會了相互尊重。
親情,不是無休止的索取和綁架,它更像一棵樹。需要陽光雨露,也需要適當的修剪,才能長得更健康,更長久。
我轉過身,看到父親正微笑地看著我,眼神里充滿了欣慰和驕傲。
窗外,新年的鐘聲敲響了。
我知道,屬於我的,一個嶄新的人生,才剛剛開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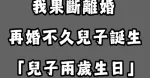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