剛同意弟弟一家來過年,老婆離家出走:8口人坐等著吃,憑什麼
直到很多年後,我才真正明白,林曉靜在我掛斷電話後,遞給我那杯涼透了的茶,究竟是什麼意思。
那杯茶,像我們十五年的婚姻,起初是滾燙的,後來變得溫吞,最後,在她轉身離開那個除夕夜時,涼得像一塊冰,直直地硌在我心口。
十五年,四千多個日夜,我習慣了她在廚房裡的背影,習慣了她把我們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條,習慣了她對我家人的無限包容。我以為那是妻子應盡的本分,是親情里不言而喻的默契。
直到那個本該闔家團圓的夜晚,八口人,三代人,圍坐在空蕩蕩的餐桌旁,面對著一桌子半成品的菜肴,和那個女人決絕離去後留下的、巨大而沉默的空洞,我才被那句無聲的質問砸得頭暈目眩——憑什麼?
是啊,憑什麼呢?
而這一切的崩塌,都始於三天前,我接起弟弟陳建業的那通電話。
第1章 一通電話與一杯涼茶
「哥,是我,建業。」
電話那頭,弟弟陳建業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帶著點大大咧咧的親熱。我正坐在沙發上看晚間新聞,曉靜在廚房裡忙活著,抽油煙機的聲音嗡嗡作響,混雜著鍋鏟碰撞的清脆聲響,勾勒出這個家最尋常的煙火氣。
「嗯,怎麼了?你那邊廠里放假了?」我把電視聲音調小了些。
「早放了!哥,跟你商量個事兒。」建業頓了頓,語氣變得有些討好,「今年過年,我們一家四口,能不能……還去你那兒過啊?」
我的心,下意識地沉了一下。
不是不歡迎,建業是我唯一的親弟弟,我們從小一起長大,感情深厚。只是……
我下意識地瞥了一眼廚房裡那個忙碌的背影。曉靜正彎著腰,仔細地清洗著一條剛買回來的鱸魚,水流聲嘩嘩作響。她的側影在廚房溫暖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柔和,但不知為何,我卻從那微微繃緊的肩背上,讀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。
「怎麼?你嫂子去年不是說……讓你們今年自己在家開火試試嗎?」我壓低了聲音,儘量讓語氣聽起來像是隨口一問。
「哎呀,哥,你又不是不知道王莉那手藝,做的菜狗都不吃!」建業在電話那頭笑了起來,聲音里滿是理所當然,「再說了,過年嘛,不就圖個熱鬧?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才叫過年。我跟爸媽都說好了,今年還跟去年一樣,年三十兒一早,我們兩家就一起過去,熱熱鬧鬧的!」
他連「爸媽」都搬出來了。
我爸媽住在離我們不遠的老小區,自打建業結婚後,每年的年夜飯,就雷打不動地在我家吃。理由很簡單:我這裡房子大點,坐得開;曉靜做菜好吃,比外麵館子都強。
起初幾年,曉靜是真心實意地高興。她是個重感情的女人,總說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齊齊。為了那頓年夜飯,她提前半個月就開始構思菜單,從網上學新菜式,除夕前兩天就開始泡發乾貨、準備食材,到了年三十兒那天,更是從早上六點就在廚房裡扎著,一直忙到晚上開席。
我不是沒看見她的辛苦。每次吃完飯,我都會摟著她的肩膀,由衷地讚嘆:「老婆,你辛苦了,做的菜真好吃,全家都誇你。」
曉得也只是笑笑,擦擦額頭的汗,說:「你們吃得開心就好。」
可這種誇讚,就像往一杯水裡撒鹽,起初還能嘗到甜頭,年復一年,鹽越撒越多,水早就變成了苦澀的滷水。
去年除夕夜,送走所有人後,曉靜累得癱在沙發上,連根手指頭都不想動。她看著滿屋子的狼藉,瓜子殼、水果皮,還有孩子們打鬧弄翻的飲料漬,眼神空洞。
「建軍,」她輕聲說,「我有點累了。明年……能不能讓他們自己家也張羅一次?哪怕就一次。」
我當時心裡咯噔一下,嘴上卻還在打哈哈:「怎麼了?累著了?明年我幫你,我給你打下手。」
曉靜沒再說話,只是沉默地起身,開始收拾殘局。那晚她的沉默,像一根細小的針,在我心裡扎了一下,不深,但有點疼。我以為這事兒就這麼過去了。
沒想到,建業的電話,又把這根針給拔了出來,帶著血。
「哥?你在聽嗎?哥?」建業的聲音把我從回憶里拽了出來。
我能怎麼說?拒絕嗎?
說我老婆累了,不想再伺候你們一大家子了?這話一出口,親兄弟的情分還要不要?爸媽那邊怎麼交代?「不孝」、「娶了媳婦忘了娘」的帽子扣下來,我陳建軍在家族裡還怎麼抬頭?
「行吧,」我聽到自己的聲音乾巴巴地響起來,「那就……來吧。早點過來。」
「好嘞!就知道我哥最大方了!那我跟王莉說了啊,讓她別準備東西了,省得浪費,反正嫂子啥都準備得妥妥帖帖的!」
建業歡天喜地地掛了電話。
我捏著手機,手心裡全是汗。客廳里新聞聯播的片頭曲已經結束了,主持人字正腔圓的聲音在空蕩的屋子裡迴響,顯得格外不真實。
抽油煙機的聲音停了。
林曉靜端著一杯茶,從廚房裡走出來,輕輕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她沒看我,眼神落在電視螢幕上,仿佛對剛才的通話內容一無所知。
「魚洗好了,明天清蒸還是紅燒?」她問,聲音平淡得像在談論天氣。
我端起茶杯,想喝口水潤潤乾澀的喉嚨。手指剛碰到杯壁,就觸電般地縮了回來。
是涼的。
不是溫吞,是那種在冬天裡放了很久,涼得徹骨的冷。
我抬頭看她,曉靜也正看著我,她的眼睛很亮,像兩口深不見底的井。那眼神里沒有憤怒,沒有質問,只有一種讓我心慌的、死寂般的平靜。
「曉靜,我……」我張了張嘴,想解釋,卻發現所有的話都堵在喉嚨里。我說什麼?說我沒法拒絕我弟?說為了我的面子,只能委屈你?
她什麼也沒說,只是微微搖了搖頭,然後轉身走進了臥室,「砰」的一聲,關上了門。
那一聲輕微的關門聲,卻像一聲驚雷,在我心裡炸開。我知道,有些東西,從我答應建業的那一刻起,就已經不一樣了。
那杯涼透了的茶,就那麼靜靜地放在茶几上,水汽在玻璃杯壁上凝結成細小的水珠,模糊了我的視線。
第2章 沉默的準備與缺席的家人
接下來的兩天,家裡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平靜。
曉靜沒有再提那通電話,也沒有跟我吵鬧,甚至連一句抱怨都沒有。她像一個被設定好程序的機器人,照常買菜、做飯、打掃衛生。只是,她不再對我笑了,話也變得極少。我們之間,仿佛隔了一層看不見的玻璃,我能看見她,卻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溫度。
我心裡憋著一股勁,既有愧疚,又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煩躁。我覺得她小題大做,不就是一頓年夜飯嗎?至於這麼跟我賭氣?但看著她沉默的側臉,我又說不出任何指責的話。
我試圖彌補。
她去菜市場,我主動開車送她。她提著大包小包回來,我趕緊迎上去接過來。她準備年貨,我就在旁邊陪著,笨手笨腳地幫她打下手。
「曉靜,這個……這個要怎麼弄?」我拿起一個豬蹄,有些無措。
她頭也不抬,淡淡地說:「放那吧,我來。」
「我幫你洗菜吧?」
「不用,你歇著吧,別把水濺得到處都是。」
她拒絕了我所有的示好,用沉默和距離,在我倆之間築起了一道高牆。
兒子陳爍似乎也察覺到了家裡的低氣壓,變得格外乖巧。他寫完作業,就安安靜靜地在自己房間看書,連最喜歡的動畫片都不吵著要看了。
年二十九這天,曉靜開始為年夜飯做最後的準備。她列了一張長長的採購清單,貼在冰箱上。我湊過去看,從波士頓龍蝦到澳洲和牛,從東星斑到象拔蚌,幾乎都是些頂級的硬菜,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豐盛、昂貴。
我心裡一喜,以為她這是想通了,打算好好露一手,把這個年過得風風光光的。
「老婆,買這麼多?太破費了吧?」我笑著說,想緩和一下氣氛。
她正在系圍裙,聞言,動作頓了一下,回過頭看我,眼神里沒什麼情緒:「你弟弟一家難得來,爸媽也在,總不能怠慢了。你不是最要面子嗎?」
這話像根軟刺,扎得我有點不舒服,但又不好發作。我只能幹笑著說:「還是我老婆想得周到。」
那天下午,我們一起去了全市最大的生鮮超市。曉靜推著購物車,目標明確地在各個區域穿梭,一樣一樣地往車裡放東西。我跟在後面,看著購物車越堆越高,心裡盤算著這一趟下來,怕是半個月的工資都得搭進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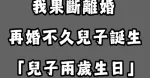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